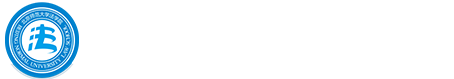2018年12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1922会议室进行了以“信息革命、社会重构与法治变革”为主题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郭殊副教授主持。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权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彭錞助理教授及北京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安然博士先后与谈。

(主题讲座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郭殊副教授)
主讲人:

(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支振锋教授的主题报告首先从历史出发,铺陈本讲座主题的预设与问题。他提到,法律是对社会生活最深刻的描摹,是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应对方案,也对社会本身产生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状态下,法治会有不同样态。按此思路,我们今天正在迎来信息革命的时代,信息革命使人类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处于重构之中,正是需要观察社会实践,探讨新理论的时刻。
随即,支振锋教授从人类社会的组织化历史、信息革命与社会再组织、信息社会的法治困境及法治的自我救赎四方面展开探讨。
一、 人类社会的组织化历史
支振锋教授首先解释了人类社会组织化的含义。他指出,人类社会组织化其实质就是将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的方式。社会的组织化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紧接着,他对人类社会从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再至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化历史进行梳理并得出结论——法治在工业社会之后得以真正的勃兴。信息革命使得国家能力得以体现,技术为人类赋能,个人与国家都强大起来。支振锋教授介绍了人类不同阶段的组织方式、基本单位和治理方式。他认为,组织方式决定治理机制。人类对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人类社会自身组织方式的变化。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联系方式,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而决定着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
二、信息革命与社会再组织
支振锋教授认为网络的价值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信息改变人的生活,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化方式。但同时,支振锋教授提出,信息社会具有两幅面孔。信息社会既是互联互通、协同进步、自由无极的大同盛世,也可能成为统治、支配、殖民、剥削的强力工具。
支振锋教授提出,信息革命将作为人的符码化的最后一环。认证与编码,也即符码化,是国家能力的基础。古代靠户籍,现代靠身份证,而信息时代,还可以用指纹、虹膜、行为习惯(位置信息、行动轨迹、肢体语言、购物记录、工作情况、网络言论)等进行数据画像。对于政府而言,被统治者前所未有的清晰和确定。这可能导致人的商品化将达到最新的境界。
支振锋教授接着谈到,信息革命下的社会面临着单向透明的信息不对称,如隐私危机。
对个人信息的搜集程度前所未有,其泄露亦前所未有。他总结到,信息革命的深化会促成渔网型总体社会的形成。人类从组织松散的渔猎社会、国家能力和统治能力不足的封建或帝制社会及个体平等、分权对抗性的现代工业社会,可能会走向个体之间愈益松散但所有个体更容易被总体性控制的总体社会。
三、信息社会的法治困境
支振锋教授首先指出了信息革命下的一系列现实法治难题,如共享经济对行政管制的挑战;智慧司法,特别是智能判决辅助系统对法院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的挑战;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无人驾驶对传统交通法规、道路设计、信号灯设计带来的挑战;互联网巨头的形成与反垄断;人工智能推荐算法所导致的舆论操纵,比如围绕美国大选的争议;互联网平台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顾客的不公平区分,比如,识别出具有不同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区别对待;人工智能的武器化等等。
同时,支振锋教授也提出了法律的“死亡”危机,即代码会不会取代规则,算法会不会取代法律、小法律、人工智能、区块链与智能合约以及主权国家的危机。进而支振锋教授也研讨了什么是人、自由何在的问题——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有可能获得情感、欲望与自由意志?于此问题,他认为,即便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成为人,更不会成为神,但在渔网型总体社会中,在信息单向透明的情况下,人类的自由仍难以全面实现。
四、 法治的自我救赎
在这一部分,支振锋教授对在信息革命的现状下法治如何自我救赎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首先法治要保卫社会、保卫个体。我们需要更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与法治,避免渔网型总体社会的形成,避免人类成为渔网中无助而又对彼此命运漠然的鱼儿。其次,他认为需要严格对科研活动的伦理与法律约束,谨慎应对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结合,阻止“神”的诞生。同时,支振锋教授认为,要以人格尊严与自由作为信息技术的边界。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何为是人的自由。法律对人的尊严与自由的保护,应该就是信息革命的底线与边界。
与谈人: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刘权副教授

刘权老师首先指出,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确有很多新的变化,对社会现实造成了很大的挑战。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平台经济是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既然平台经济是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经济基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现有的法治体系需要革新。刘权老师认为,不能够全盘否定以往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确实存在很多缺陷、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关于社会再组织,刘权老师认为,在信息社会社会组织发生了很多变化,典型的是互联网组织、互联网平台的兴起,虽然平台也是公司,但是它不同于传统的公司组织形态。以往政府对线下的店铺进行直接监管,如质检部门对线下店铺进行现场检查和产品抽查。但现在成千上万的卖家都移至线上,由平台对其进行治理,平台充当着政府的很多监管职能,制定规则、执行措施并解决纠纷。刘权副教授认为,对于这种新型的组织,将来需要引入新的法律理念进行规范,适当引入公法的原理和制度,把规范国家公权力的一些理念适当引入进来。如正当程序原则,平台制定规则时、管理线上店铺时应当遵守正当程序,说明理由、听取陈述与申辩。在实体上也应当引入比例原则等对平台进行约束。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刘权老师提出,传统上依靠隐私权来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在信息社会,单纯靠隐私权可能无法全面保护个人权益。例如人脸、指纹、虹膜等信息很难归结为隐私,但属于个人信息,需要新型的保障机制。他认为,可以适当确立个人信息权,虽然个人不能够完全像控制传统物权那样有效控制个人信息,但确立了个人信息权之后,更能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权利。
刘权老师接着谈到共享经济监管的困境。他指出,现在争议较大的是共享经济企业的劳工权益保障。如网约车司机的劳工权益如何保障,应不应当像对待传统出租车司机一样对待网约车司机。刘权副教授认为,如果按传统的雇佣关系来理解共享经济平台与司机的关系,确实会对共享经济平台造成过大的负担。但若完全无保障,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隐患。
刘权老师最后总结到,在信息社会,基本的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法治体系确实需要进行变革。在进行变革时,应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类的关系,人格尊严与自由需要成为技术的边界,技术发展必须以保障人格尊严和自由为终极目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彭錞助理教授

彭錞老师从另一角度进行了与谈,他从支振锋教授的讲座内容中析出三位思想家之观点,并予以进行阐释。首先是马克思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进行分析,一方面要对简单的决定论有一定警惕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马克思其终极的对人的自由的追问。比如,是不是到了信息社会,人类就一定会走向某种情形的组织化。他认为,在能否依据理论直接推演出未来一定会走向渔网社会的问题上,有更丰富的内涵可以讨论。他同时提出,如果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向,一定要注意马克思终端的指向,即自由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位是福柯。他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转述福柯的观点,即于无声处听惊雷。看似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更自由,但是这可能只是一种新的宰制技术,而且它是深入我们身体和灵魂的权力技术。同时福柯其追求自由的想法与做法也与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
第三位康德。他指出,在康德的观念中,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是同一的,人的尊严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支振锋教授所提到的,强调人的自由与尊严作为技术发展的边界,实际上为我们立了一个界碑。但他认为,无论是人的自由还是人的尊严,从历史发展来看,都是建构的结果。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工业社会下的人对于自由、对于自我的理解是不同的。他提出,我们可以思考与设想,将来的信息社会,我们对自由和尊严的界定本身是否可能发生变化,是否有可能在人们的所有的需求都轻易就被满足的情况下,人们放弃了自由观和尊严观。若有那时,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便不构成问题。
彭錞老师总结到,对于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去守住“界碑”,他保持着并非悲观的态度。他以核弹的发明为例,人类在发明核弹之后,至少到今天还维持着整体上的“恐怖均衡”,说明人类社会有共同之努力。因此就这个意义上,人类不会自陷风险去流浪地球。即便流浪地球,人类社会也有去维系最后尊严和自由的勇气和智慧。因此一方面要认真倾听支振锋教授之警醒,另一方面也要保留对于未来的一线希望。
北京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安然博士

安然老师结合自身工作内容及经验进行了与谈。首先,安然老师以报刊的更新为例,她指出,对于新问题,要善于发现,更要快速形成对新问题的基本回应思路,保持对问题的敏锐度。
安然老师认为,本场讲座实质上围绕着“脑力”一词。工业革命扩展的是人们的体力,给予人们更多物质财富。而信息革命可能带来更多的就是脑力挑战,很多问题还是需要人类的智慧去应对,包括治理方式的变革等等。结合自身工作,她扩展谈及论文撰写时的“问题意识”。她认为,能够作为论文选题的问题,一定是在实践运转中暴露出的问题,是现实、客观的,这样的问题值得运用学术技巧、理论方法去解决。问题绝非论文作者自己凭空幻想而来,比如如一部法律、一项制度刚刚颁行,只因其未按原来学界所设想,就认为其有问题,这种“问题意识”不切实际。同时她也提出,讲究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把问题简单抛出,而要运用理论和逻辑将其论证并解决。

(讲座嘉宾合影)

(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学生提问:
1.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使得每个人都拥有发布权,这是否也是信息革命对未来统治的一个挑战?
支振锋教授:首先,区块链内的信息并非无法更改,通过对节点比例的设计可以规制链上信息。第二,区块链上链之前的信息是可变的。同时,区块链高度依赖算力、存储和电力,如果所有人都用区块链的话,资源是否充足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其将来如何发展,现在并不能做出定论,需要不断去观察,以后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2.信息革命时代的“渔网型总体社会”跟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是否是殊途同归,您怎样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支振锋教授:其实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社会之后,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不是民主削弱了社会,是民主增强了国家能力。但是民主的前提是社会的自主,是基层的自治。西方的社会一直就是有契约论的传统,而最典型的契约建国的就是美国。托克维尔有几个重要的发现,比如美国如何组织成国家,具体是因为有很好的基层自治。建议同学再读一读托克维尔的论著,民主和渔网型总体社会是非常不同的,民主是分布式的,而网络社会中分布式掩藏的是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