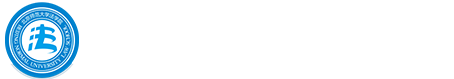当前,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问题是我国学术界的热点之一。2019年4月26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我国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案“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首次以判决的形式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了探索,给学术讨论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实例。案件虽已审结,但对问题的探索没有到尽头。为了充分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相关法律问题,了解学术界、实务界的不同观点,同时便于法律同仁的深入交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网络与智慧社会法治研究中心举办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相关法律问题研讨会”,于2019年5月23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1822召开。多名学术界专家和实务界法官、律师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围绕着“菲林律所诉百度案”及人工智能相关法律问题展开,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的法律地位、权利归属和保护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柴荣教授首先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向各位嘉宾致欢迎辞。柴荣教授回顾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发展历程,高度肯定了法学院全体教师的辛勤努力,对嘉宾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同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会议进入正式议程,北京互联网法院卢正新法官首先发言。卢正新法官作为“菲林律所诉百度”案的主审法官,对案情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阐述了判决的相关思路。卢法官认为,法官不能拒绝审判,对案件进行裁判是法院、法官的本职工作。然而现行法律缺乏对软件或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内容著作权的直接规定,自然人创作完成仍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同时,涉案分析报告虽有一定独创性,但并非是软件用户感情、思想的独创性表达,因此不能将分析报告认定为作品。卢法官也认为,虽然分析报告不构成作品,但由于软件使用者进行了一定投入,软件使用者应当享有一定权益。

北京大学法学院杨明教授随后发言。杨明教授从人工智能的定义展开,认为人工智能的核心仍属于能力,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还不是主体,也无必要以主体对待。在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不是作品时,应该先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先考察是否有作者。类比摄影与相机之间的关系,杨明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同样是创作的工具,作品权利与人工智能无关。权利归属的本质是赋权,杨明教授引用科斯的理论,认为赋权就是对信息为外部所知的原因力的安排,所有赋权的目的都是服务于交易,所以后续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因力应当被赋权。最后,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特殊性上,杨明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比一般意义上的作品没有特殊性,未改变由人创作的事实,只是外部力量介入的方式有了一些变化,但创作的根本还是自然人。

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互联网司法研究中心宋健宝主任认为,第一,人工智能是否能成为作者。是否先评判作者还是先评判什么构成作品,哪一种分析比较方便,这是一个裁判思路的问题。第二是个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表现形式是一篇文章,从文章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对有独创性的部分进行保护。第三,根据这个案件,更应该好好考虑人工智能著作权的概念。至于这个案件,实际上就是向检索软件输入关键词,最后生成一个报告。独创性也好,原创想也好,他必须有一个思想。而人工智能中,相同的输入经过软件以后输出,如果数据库本身不更新,输出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了他们的表达是具有确定的。这也是人工智能和人的思想不能相比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以后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形成合力可能成为将来司法要面对的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腾讯研究院张钦坤秘书长随后发言。张钦坤从腾讯自身的实践出发,向与会专家提出问题:腾讯在新闻领域如体育新闻使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自动写作,从软件开发到软件使用再到内容发送在腾讯公司内部形成闭环,那么新闻的作者是谁?杨明教授回答道,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也属于创作,其过程必然有人力介入,对新闻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应享有著作权。宋健宝主任回答,他同意“菲林律所诉百度”案判决书的逻辑,在目前法律下,此类新闻不构成作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夏扬教授则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的表述并不一定是唯一性的,是否将人工智能设置为主体只是法律技术的问题,在传统法律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解决成本过大时,立法承认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或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吴沈括副教授发言认为,这个话题特别新,而且特别有价值,在目前很多情况的处理下,这个判例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也体现出司法机关的创新,在刑事司法中特别明显。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生成这个案例中,吴沈括副教授认为:在这个案件中,要考虑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属性,可能需要判断两层面的问题,第一层次是强人工智能,第二个层次是弱人工智能。随后吴沈括副教授还从数据流转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从数据的输入、数据的处理到最后数据的生成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基于现有的网络安全法,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处理者有保护完整和保密义务,处理者对这个完整性有法律责任。“菲林律所诉百度”案中,被告实际上侵害了原告数据的完整性。
清华大学法学院吴伟光副教授随后发言。首先,吴伟光副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无需赋予主体地位。其次,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应当先分析作品再分析作者。独创性是是否构成作品的判断标准,主观独创性标准违背了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平等的原则,应当采用客观标准。独创性在著作权中的功能是识别作品,人工干预越多,独创性就越强。然而随着时代变化,标准化程度日益提高,独创性要求的高低也在发生变化。若以独创性的高低论是否是作品,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就要面对无数种个案情况,不仅制度成本高昂,而且难以实现。独创性越低,经济成本就越低,制度成本也越低。人工智能生成物虽然独创性不高,但仍然属于作品。

华为大中华终端高端法务部部长王高明律师认为,通过这个案例,思考到了作品完整性、署名权,创造性的提出了相关的权益,对于相关权益付出人的利益,对于权属收益进行分配 ,通过立法司法进行保护。对于责任的问题,也需要从立法、司法角度进行思考。 从一个企业角度来看,不管是人工智能作品和人工智能生成物,都需要对于相关权益进行保护,激励人工智能后面付出劳动的人。

百度法务部徐佳航律师结合自己的一些认识和域外的一些经验,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和问题。第一 当下人工智能的概念到底是什么,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概念是不是应该重新定义。第二,人工智能对版权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已经在无时无刻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保护数据,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规定。第三,人工智能的权利归属问题。因为这个过程离不开开发者的努力。同时,构成著作权的作品有著作权法的保护,如果构不成著作权中的作品,那该如何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吉豫副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工具,其发展并不一定需要模拟人类的思考,不必以人类的思维来看待人工智能的创作。从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创作没有明显违背著作权法的精神。但张吉豫副教授也对人工智能创作有担忧,人工智能创作的强大,是否会抑制人的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夏扬教授认为,法官本来就是以一个保守的态度来面对社会现实。通过这个案件,怎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做出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合理判决,在这个案件中看到了卢法官的智慧。今天讨论的更多的是这个案件引发出来一些人工智能的其他问题。主体问题,独创性问题,作品的定义等等。近年来英美法的影响越来越让人接受,法人也可以成为著作权的主体,这对著作权法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拟制人格也并非将之人格化。夏扬教授认为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著作权法同样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或许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网络与智慧社会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亚太人工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刘德良教授最后发言。首先,刘德良教授提出,对于人工智能在法律上是否应该赋予其主体地位问题的回答,应该从人类发展人工智能的初衷,即为何要发展人工智能的角度上考虑。在此基础上,就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的问题了。毫无疑问,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宗旨是提高生产力,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使人类获得更大、更多的自由,而不是取代人类,使人类成为被奴隶的对象。因此,安全可控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人工智能的基本准则;不安全、不可控的人工智能不应当被发展,应该受到控制乃至禁止。为此,必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制性要求人工智能的算法必须公开,接受整个人类社会的监督;同时对人工智能产品有关的实行市场准入,只有软硬件都符合技术标准的人工智能产品才能进入市场;二是法律上拒绝承认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
对于算法公开问题,刘德良教授认为,算法公开显然会遭受一些先进公司和技术强国的反对。技术先进的人工智能公司和国家则往往以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为借口拒绝公开其算法,从而实现保持竞争优势的目的。而学术界,尤其是主流法学界,要么是没有看到安全可控是整个人类发展人工智能的基本准则,要么是出于优先发展本国技术的想法,继续秉持传统的思维将人工智能算法视为商业秘密。这种观念及其产业政策和立法的后果将有悖于安全可控这一基本准则的落实,进而最终导致人类发展人工智能事与愿违。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或主体资格问题,刘德良教授指出,目前,很多学者由于没有从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工智能这一根本立场出发去思考,而是基于功利的思维,认为应该按照公司理论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显然,这种观点并没有看到人工智能与公司的本质区别:公司是自然人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其无法自主行为,必须借助于自然人的行为来实现其行为目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规范人的行为来实现规范公司行为的目的。而人工智能则不然,一旦赋予其独立的主体资格,那么,通用型、超强人工智能或有独立意识的人工智能,就完全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去实现自己而非其所有人的利益。如此以来,必将跟人类发生冲突,最终将取代人类,人类也将因此而面临由主体沦落为客体的境地。
其次,刘德良教授指出,目前,之所以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属性存在分歧和认识偏差,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缺乏应有的认知。实际上,目前的人工智能往往功能单一,不同类型(功能)的人工智能,其工作原理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不能以对一种功能(类型)的人工智能工作原理的认知来代替对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的认知。目前的人工智能,不仅在其算法设计出来后需要用大量的数据对其进行训练,即使在人工智能的后续使用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地给予新的数据来训练它,以实现其不断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有的人工智能还可以自主学习,从而获得新的智能。因此,那种认为人工智能一旦设计出来后,无需再用数据训练,或者不会自主学习,从而“相同的输入,必将产生相同的输出”,其结果,人工智能生成物一定不符合版权法上的独创性要件的见解是不成立的。
最后,刘德良教授指出,对于利用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内容或成果(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应该首先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内容本身是否符合版权法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如果符合,它就是作品,就应该受版权法保护,其权利主体属于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所有。那种先从生成物是人工智能而非自然人完成的,而版权法上作品的创作时自然人的创作,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就不是版权法上的作品的观点,不受版权法保护,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户或使用者就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人的观点是违背了人类发展人工智能的初衷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由此,北京互联网法院没有将本案所涉人工智能生成物认定为版权法上作品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如果按照法官判决中所遵循的逻辑,对于相同的“生成物”,如果我们(原告)不表(标)明是利用人工智能产生的,那么,如果它符合作品的要件,就应该被认定为作品,我们(原告)成为版权人就是毋庸置疑的。显然,但从逻辑上看,本案法官的思维也是有问题的。

至此,本次学术研讨会顺利闭幕。此次学术研讨会给各界专家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与会嘉宾从实务到理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精彩纷呈。本次会议发起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网络与智慧社会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教授表示,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希望在未来有更多与法律同仁们深入交流的机会。